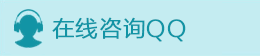翻译可以达到尽善尽美吗?
可能的。因为,如果说某一个翻译作品不完美或说某一作品有这种或那种缺点的话,那我们就有可能克服这些缺点。但事实上,迄今为止,我们恐怕还难以找到这种所谓“没有一点儿缺点”的翻译。客观地说,我们也许永远也无法找到尽善尽美的翻译。以下我们尝试从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
一 翻译标准难以统一
从共时的层面看,小至个人,大至流派、文化群落,对于翻译标准显然有着不同的看法,尽管我们并不否认这些标准中也有许多共同的东西。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中关于翻译标准的论述。中国古代翻译理论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文”、“质”之争。梁启超曾说:“好文好质,隐表南北气分之殊。虽谓直译意译两派,自汉代已对峙可耳。”[1] “文”、“质”之争实际反映的是两派对于翻译标准的论争。到了近代,关于翻译标准的论述最有影响的当然是严复。他提出的“信”、“达”、“雅”的主张长期被奉为理论圭臬。但即便如此,严复的标准也不是人人都赞同。陈西滢就曾指出:“雅,在非文学的作品里,根本就用不着⋯⋯达字也并不是必
要的条件。”[2 ]谈到现代翻译理论,我们不能不提及赵景深和鲁迅。鲁迅曾将赵氏的观点归纳为“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并
对此进行了回击,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观点[1 ] (第296 页) 。不过,鲁迅的“宁信而不顺”的观点并不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在当时主要是针对赵景深错误观点的一种反驳,这一点是有必要交代清楚的。
当代中国翻译理论更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关于翻译标准可谓是众说纷纭。许渊冲在评价当代中国翻译理论时就曾指出:“20 世纪中国文学翻译的主要矛盾,在我看来,是直译与意译,形似与神似,信达雅(或信达优) 与信达切的矛盾。”[2 ]这实际上表明了翻译标准难以达到统一的现实。综上所述,不管在历史的哪一阶段,翻译标准从来就没有统一过,而且,将来也不可能有统一的翻译标准,因为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是不同的,而且,即使是同一个人对于事物的认识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共时的层面上也会有程度不等的共同认识;我们只是强调,由于诸多因素的作用,人们对于翻译标准的看法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既然翻译的标准不同,人们对译文的评价也就不可能一样。这样一来,所谓“尽善尽美”的译文其实也就并不存在,或说,有人认为“尽善尽美”的译文,别人也许并不以为然。从历时的层面看,翻译标准的不同就更难避免,因为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翻译内容。例如:东汉至唐宋间侧重佛经翻译,明末清初侧重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侧重文学与哲学的翻译,而改革开放后则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各种完全不同的内容,只要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便都有翻译的可能。由于翻译的内容不同,人们对于翻译的认识就不可能完全相同,因而,关于翻译标准的论述自然也就不同。关于这一点,我们刚刚已经谈到,故不赘述。
在西方,关于翻译的标准历来争论颇多。早在1790 年,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 在其《论翻译的原则》(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一书中就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第一,译文应完全复写原作的思想;第二,译文的风格和笔调与原作具有相同的特征;第三,译文应和原作同样流畅自然。这实际上就是泰特勒的翻译标准[3 ] (第35 - 40 页) 。这一关于翻译标准的论述与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有颇多相似之处。在这三个原则中,作者显然比较强调类似于严复“信”的原则。
此后,前苏联的费道罗夫在其1953 年出版的《翻译理论概要》一书中第一次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等值”理论。在这一理论中费道罗夫还特别提到了полносценностъ,它有两个意思: (1) 与原文作用相符(表达方面的确切) ; (2) 译者选用的语言材料的确切(语言和文体的确切) [4 ] 。
关于翻译标准的论述,近年来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还有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 Eugene A. Nida) 提出的“动态
对等”理论。在奈达与Tabor 合著的《翻译理论与实践》(The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1974 edition) 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
Translation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to the source language message , firstly in terms of meaning ,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 (翻译就是在译入语中再现与原语的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物,首先是就意义而言,其次是就文体而言。) [5 ]后来,奈达又将“动态对等”改为“功能对等”(functional e2 quivalent) ,强调信息内容和形式都要尽可能对等。
综观西方翻译理论,我们发现它们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它们都强调要忠实于原文,这与中国翻译理论中严复的“信”是一致的。不过,泰特勒更强调对原文的忠实,而费道罗夫除强调“信”以外,还特别强调“达”,即准确性。奈达则强调“意义和文体的对等”。奈达还指出:“翻译的原则不在求两种语言形式上的相当(formal correspondence) ,而在求译文受众与原文受众在反应上的基本一致。”[
2 ] (第132 页)总的来说,无论中国翻译理论还是西方翻译理论,都有诸多共同之处。不过,我们在此要强调的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翻译标准历来都是最有争议,看似相近,而实际上又很难达至共同结论的一个问题。因而,大家对于译作的评价很难有共同的声音,当然就更谈不上译作“尽善尽美”的问题了。
二 译者个体因素的不同
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译者的个人因素会使其译文呈现出个人特色。而其译文又或多或少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其实,阻碍个人译文达到完美的因素很多,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 译者对作品的理解
译者对作品的理解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首先是自身的因素。众所周知,要翻译一部作品,译者不仅要有足够的外语能力,而且对文化须有足够的了解。而文化一方面有那个时代以前的积淀,另一方面又会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这样,译者在翻译时就须考虑到作品的文化背景,把属于某一时代的作品放到另一文化背景下考察显然是不合适的。但对于具体的译者而言,他所受的教育并不能保证他对原语文化有足够的了解。如果真有译者对其翻译所涉及的两种语言的文化都有足够的了解,那他一定是很幸运的,因为事实上,极少有人既有本族文化的背景,又熟谙原语文化。我们之所以强调文化对于理解作品的重要性,是因为文学作品本身就是文化的反映。很难想象,没有一点莎士比亚时代的背景知识,译者便能只通过对语言的认知成功地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
(二) 译者对作品的表达
在理解原作的基础上,译者对作品的表达通常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是译者驾驭语言的能力。译者必须既熟悉母语的特点,又熟悉外语的特点,这样才能保证在翻译时找到恰如其分的语言材料表达原语作品的内涵。但事实上,我们会遗憾地发现,有的人外语水平或许很高,而母语的基本功不太扎实;有的人母语基本功还算扎实,但外语水平又有些欠缺。不管哪种情况,都会影响译者对作品的表达。其次,译者应该有起码的道德和责任心。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我们对原作都应抱实事求是的态度。试图改变原作的意图、风格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道德的。要么就不翻译,要么实事求是,这应该成为翻译工作者的基本原则。但要让所有的译者都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有些译者由于自身的原因和外界因素的干扰,有可能置原作的品味于不顾,这种情况在翻译界并非没有。结果,我们发现:同一部作品,在翻译成目的语之后,有可能是大相径庭的。本来,一部作品,不同的人翻译肯定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一部作品的品味、风格总应该大致是相似的吧。如果连对作品的基本共识都没有,翻译出来的作品就很难取得别人的认同,更不用说什么尽善尽美了。
(三) 对译文受众期待的理解
一般说来,读者对译者和译文都有某种程度的期待。一方面,译文受众希望译者能将浸润了外域文化的作品以他们能接受的某种方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读者也希望译文应该既有外域的风味,又必须在他们的理解范围之内,同时还希望译文不露出牵强生硬的痕迹。对译者来说,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因为:首先,受众的期待是往往不同的;其次,对译者而言,他不可能了解全部受众的期待和受众的全部期待。这也就意味着,译者只能考虑到部分受众的部分期待,
剩下的那一部分他就只能依据自己的判断。毫无疑问,译者会把这种判断融入到自己对作品的整个思考中并最终在译作中体现出来。这样看来,译者的理解和表达并不一定完全是受众期待的。因而受众对于译作的评价自然也就会产生形形色色的差异。
总的说来,译者个体因素的不同在翻译中最直接地反映为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和表达以及对受众期待的理解的不同。由于译者的特殊作用,译者长期处于异常困难的境地。一个无论怎么好的译者在动手翻译一部作品的时候都要冒一定程度的风险。因为他对作品的理解会决定整个作品会以怎样的形式出现在受众面前。既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个体的因素有如此多的不同,我们也就无法让译文受众对一部译作作出“尽善尽美”的评价。
三 从辩证角度看“尽善尽美”
关于翻译能否达到尽善尽美,以上我们已从翻译标准和译者个体因素两方面加以探讨。实际上,如果从辩证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翻译永远都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
(一) 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 牵涉到的层面极广,环节极多要保证每一层面、每一环节的精确性和可靠性,即“没有一点儿缺点”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译者不可能有如此多的精力去精通如此多的环节,即便他有扎实的母语基本功和足够的外语能力,他也无法保证熟知所翻译的每一部作品的所有的历史和文化的背景。这样,他对作品的理解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偏差。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接受译者的译文,并不是因为译者的理解和表达全无问题,而是因为读者无法了解也没有必要去了解关于这部作品的全部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我们能容忍译者实际上并不完美的译文,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就是翻译的现实,我们有可能使情况变得更好,但不可能使之达到尽善尽美。
(二) 从无限发展的观点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人
们对于翻译的认识会越来越深,越来越全面,从而使翻译的水平会不断提高 读者的欣赏水平在不断提高,对于翻译标准的看法也就会发生改变。即便在某一历史阶段人们对于翻译的标准能达到相对同一,这种同一也只是暂时的。由于事物在历史中具有不可改变的发生变化的性质,所以即使我们讨论翻译的尽善尽美也只能是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之内进行。除此之外,我们要讨论这一问题将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三) 翻译不可能总是停留在某一水平上,但具体的翻译实践总是发生在某一具体的历史阶段虽然从理论上讲,在这一历史阶段,作为整体的翻译可以达到一个最高的水平,但由于整体的翻译水平并不是个体翻译水平的简单相加,所以实际上,这最高的翻译水平是无法实现的。况且,即便这理论上的最高水平我们也很难说就是尽善尽美的。
(四) 既然现实中的翻译无法达到“尽善尽美”,那么要将“尽善尽美”确立为翻译的目标就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该抱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即翻译应该建立在可以容忍损失的基础上。从长期的翻译历史看,我们的确无法拿出所谓“尽善尽美”的译作,但我们大可不
必为此而感到悲观,因为毕竟我们还可以拿出大家公认的优秀译作。认清这一现实对我们的翻译事业尤为重要。盲目地批评译作,发现译作在某一方面有某种缺陷就要一棍子将别人打死的做法只能让更多的人将翻译视为畏途。我们期待作品尽可能地走向完美,同样也期待客观公正的翻译批评。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只要文字的差别不消失,文化的差别不消失,翻译都将是一项不会消失的事业。而对于翻译本身而言,它又是一项创造性的事业。创造就意味着对旧的东西的突破,但这突破是渐进的,并且是在长期的过程中通过个体的突破得以实现的。毫无疑问,正是个体的实践才使得翻译显示出勃勃的生机。个体的实践永远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从而翻译也永远无法达到尽善尽美。显然,我们无须为此
感到遗憾,相反,我们应该为永不间断地追求尽善尽美的过程而感到自豪。因为,正是千千万万个人的努力才让翻译充满魅力,也使得翻译成为越来越被人了解和受人尊重的事业。